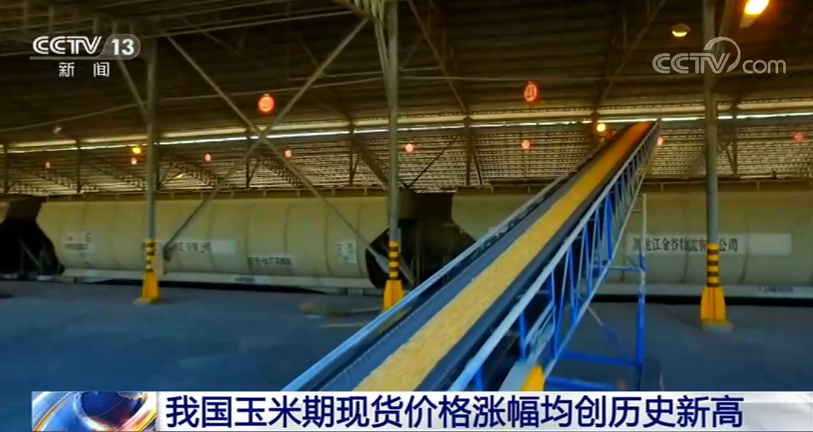霍金悖论(上)
顶尖科学家何以会是反哲学的哲学盲?
2018年3月14日,一生饱受渐冻症困扰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逝世,诸多纪念文章应声出炉。霍金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的身残志坚是对无数人的巨大激励;《时间简史》令许多非专业读者爱不释手;黑洞辐射理论虽然排不进当代理论物理最重量级发现的行列,毕竟仍是巨大的学术成果,而且若非斯疾所限,他肯定能在学术上走得更远;除此之外,霍金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从毕生致力推动性别平等,到联名反对伊拉克战争、声援以色列境内遭到歧视的巴勒斯坦人,就算与他政见不同者,也不能不肯认他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持之以恒的担当。
不过,在所有这些成就与伟大之外,本文想讨论的,却是在霍金(以及许多当代顶尖的科学家)身上以不同程度体现、但平日不大为人关注的两个问题。我将这两个问题都称为「霍金悖论」(the Hawking paradoxes),以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可称为「霍金的智识悖论」,第二个问题则是「霍金的社会悖论」。
一
霍金的智识悖论,以及科学家眼中的哲学
所谓「霍金的智识悖论」是指:为什么以霍金为代表的许多当代顶尖的科学家,无论智识与成就都卓尔不群,却往往在涉及与科学或有关或无关的哲学问题时,一方面相当外行,另一方面又对此毫不自知,不但热衷在哲学问题上公开发表外行言论,而且热衷于宣称科学可以(甚至已经)将哲学取代或消灭?
换句话说,为什么如此杰出的科学家,会既是哲学盲(philosophically illiterate)、同时又反哲学(anti-philosophy)?
相信不少人会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科学家与小说家斯诺(C. P. Snow)20世纪50年代就已观察到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之间隔阂的翻版吗,何至于现在再炒冷饭?也有人会说: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科学家不懂哲学,哲学家不懂科学,自然科学家不懂社会科学,物理学家不懂生物学,天经地义,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人(比如霍金自己)会说:什么对哲学外行不外行,哲学明明早就被科学淘汰了好吗!
这些反应,其实同样是上述悖论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人们对哲学的性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普遍误解。
首先可以注意到,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强调的是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对立;他举的例子是,人文学者往往不懂(而且拒绝了解)热力学定律,科学家往往不读(而且拒绝关心)莎士比亚。
可是,就算一位由衷看不起莎士比亚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的科学家,也不会因为自己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而自居莎士比亚专家、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如何理解莎士比亚某部剧本里的某段情节」的问题上指手画脚。
然而不少科学家对哲学的态度,却往往远不止于其对人文艺术的那种漠不关心、敬而远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也不止于(科学内部)一些自然科学家看不起「不够严密」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一些经济学家看不起「不够定量」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乃至(哲学内部)一些形而上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看不起「不够硬核」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诸如此类的学科优越感。
毕竟,所有这些优越感,都是以承认对方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本身的正当性,以及自己在对方领域内的非专业性为前提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比拼领域之间的高下优劣;就如富国虽然看不起穷国,却并不因此不承认穷国的主权地位,也并不因此自认为对穷国的民情了如指掌。
然而,对于哲学,当代不少科学家往往拒绝承认其具有独立于科学之外的领土和主权:哲学也许曾经建立过显赫一时的王朝,但它早已被异军突起的科学王朝颠覆并取而代之,后者在建立政权的战争中节节胜利,迅速接收和平定了前者治下广袤的疆域,并按部就班地搜查和清洗着境内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前朝遗老。
哲学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科学早已淘汰了哲学,所有哲学问题都能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这才是当代科学界对哲学的普遍看法;譬如公众熟知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天文学家尼尔·泰森(Neil Tyson)等等,都常常表露此类反哲学态度。至于霍金本人,更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的开篇劈头宣布:
「我们该当如何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宇宙如何运作?现实的本质是什么?所有这一切来自何处?宇宙需要造物主吗?……传统上这些问题由哲学来回答,但是哲学已经死了。哲学没能跟上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科学家如今成了我们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的举火者。」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How does the universe beha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Where did all this come from? Did the universe need a creator? … Traditionally these are questions for philosophy, but philosophy is dead. Philosophy has not kept up with modern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particularly physics. Scientists have become the bearers of the torch of discovery in our quest for knowledge.”
诚然,霍金这段话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中,确实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的经验知识(empirical knowledge)或描述性真理(descriptive truth),这部分工作必须交由科学来完成;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先后从哲学思辨对「原型科学想法」(proto-scientific ideas)的孵化中脱胎并独立发展,以及哲学对自身研究领域范围的不断再认识与再调整,乃是人类求知的必经之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功能仅限于对「原型科学想法」的孵化(然后将其移交给科学),也不意味着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或者声称但凡科学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甚至干脆是伪问题。
要明白为何如此,关键在于理解哲学问题与哲学研究的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不过在解释这一概念之前,我将先从霍金所认为「传统上由哲学回答、但如今已由科学解决」的问题中,取出一例略加分析,以便更加直观地展示霍金错在何处。
二
作为哲学盲的科学家:以霍金论「上帝有无」为例
如前引段落所示,霍金认为哲学家无力回答关于「造物主」(上帝)的问题,因此到了该由科学家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与许多知名科学家一样,霍金一生积极参与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公共争论;他本人所持的立场也有所演进,早年更接近于不可知论,晚年则逐渐坚定地转向了无神论。然而宣称「哲学已死」的霍金对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证明」,在哲学从业者看来,其实才是闭门造车而又不堪大用。
这并不是说哲学从业者们都相信上帝存在。恰恰相反,正如我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提到过的,就西方国家的相关调查而言:当代普通公众绝大多数都是有神论者;当代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程度远低于普通公众,无神论、不可知论、有神论的比例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而当代哲学家则比科学家更进一步,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其比例甚至超过科学家里无神论与不可知论的比例之和,极少有哲学家是不可知论者或有神论者。
为何哲学家对「上帝存在」这一命题的拒绝比科学家更为普遍和决绝?原因恰恰在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比霍金们深入得多。
霍金对上帝有无的思考,主要围绕如何回应「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而展开。所谓「宇宙论论证」,是传统上用来主张上帝存在的一类推理,其大致思路是: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总得有其肇因(cause)和开端(beginning),但是如果我们一步步回溯上去,宇宙本身的肇因和开端又在哪里呢?倘若我们不想陷入无穷倒退,便只能相信存在某个必然的、自在自为的、超越于宇宙万事万物以及时间本身之上的永恒造物,是为一切肇因的肇因,一切开端的开端。
对此,霍金的回应大体如下: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时间在极端条件下可以表现得如同空间的另一个维度,从而令日常所谓「时间先后」、「肇因」、「开端」等概念失去意义;奇点「以前」正具备这样的极端条件,时空在量子层面随机涨落,一般物理法则不再适用;我们身处的宇宙从这些涨落中随机诞生,没有「肇因」也没有「开端」,是以不再需要由一个自在必然的造物来预先推动这一切的发生。
然而霍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应其实已经预设了若干哲学前提,而这些预设成立与否,恰恰也是历来争论的一部分。比如,除非我们认为肇因必然在时间上先于(temporally prior to)其效果(effect)、不存在非时间性的因果作用(atemporal causation),否则凭什么不能在时间箭头失效处(奇点「以前」)继续谈论肇因?然而「非时间性」(atemporality)或者说「超越于时间之上」,恰恰是不少论敌试图赋予造物主的属性之一。
同样,对于奇点「以前」的量子涨落,有神论者仍然可以追问:这种状态之所以可能,又是出于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凭什么将其视为毋须给出进一步解释的「原生事实」(brute facts),就像以往某些反对「宇宙论论证」者将宇宙本身的存在视为毋须给出进一步解释的原生事实一样?
换句话说,霍金充其量只是回应了最初级版本的「宇宙论论证」,却没有回应(并且根本不知道)早已存在升级版的「宇宙论论证」,以及哲学家们对升级版的回应、再升级、再回应、再再……。
比如围绕肇因概念,哲学家会进一步区分「能动者因果作用」(agent causation)和「事件因果作用」(event causation),然后辨析前一概念是否成立,或者说「一个能动者(比如上帝)仅凭自身的能动性、不依赖于任何具体事件,而驱动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因果链条」这种陈述,究竟有没有任何意义;又比如有哲学家指出在宇宙论层面,事实简洁度(factual simplicity)与解释简洁度(explanatory simplicity)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因此当有神论者攻击「原生事实」缺乏简洁性、试图用「上帝存在」的假设来统合与解释时,他们其实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理论优势,相应的攻击也并没有起到他们预想的效果;诸如此类。诚然,当代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宇宙论论证」从根本上是失败的,但这种判断并不依赖于霍金的助攻。
更何况,「宇宙论论证」只是关于上帝有无的当代哲学争论中,相对次要的一条线索。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长期相互诘难中,双方在攻防上已经形成一些基本的套路:除了「宇宙论论证」之外,有神论者还试图通过「本体论论证」、「目的论论证」、「道德论证」、「证言论证」、「认知担保论证」、「反自然主义演化论证」来给无神论制造麻烦;无神论者则使用「经验性论证」、「简约性论证」、「全能悖论」、「游叙弗伦困境」、「罪恶及苦难问题」等等来挑战有神论。
前面提到,当代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经过对所有这些论证的不同版本的反复推敲,哲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有神论方的进攻套路,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破绽,缺乏预想中的杀伤力(因此在有神论与不可知论之间,不可知论更占上风),而无神论方的某些诘难手段,却能够对有神论构成根本的困难(因此应当进一步接受无神论,而不仅仅是不可知论)。当然,这并不是说持有神论立场的哲学家已经一个不剩,而是说就哲学界的总体情况而言,这场战役的胜负已见分晓。
在这样的背景下,霍金对最初级版本的「宇宙论论证」的回应,结合其对「哲学已死」的断言,便愈发显得缺乏自知之明。就好比两军作战,已经到了甲国丢盔弃甲望风而逃、乙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收尾阶段,此时乙国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姗姗来迟,身穿纸甲手持竹刀,登上安全线内的一座城楼,四下睥睨,傲然叹道:「多亏俺们弟兄几人及时赶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住了两军必争的这处要塞!」
三
哲学的规范性
以上站在无神论立场对当代哲学整体状况的评判,想必会令许多有神论者不满。毕竟有神论哲学家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输掉整场战争,而是仍在努力修补旧论证或开发新论证,从未放弃绝地反击一举扭转战局的希望。——当然,有神论者更不会认为霍金的论证是成功的,所以双方至少在「霍金不懂哲学」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而无神论哲学家对霍金的不满,恰恰在于他过分简单粗糙的论证(加上他巨大的影响力),为向公众宣传有神论者提供了可以轻松攻击的靶子:「看,无神论者的论证如此糟糕」。
所以究竟为什么,像霍金这样绝顶聪明的大脑,会在他毕生关心、倾力思考的上帝有无问题上,止步于入门级别而不自知?
如本文一开始所说,隔行如隔山、当代学术培养的专业化和壁垒化,固然可以解释霍金们对既有哲学讨论的无知:就像自然科学家不懂社会科学、物理学家不懂生物学、经济学家不懂社会学一样,科学家不懂哲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事实上,对科学一窍不通的哲学家也大有人在。——但光是这点却无法解释,科学家群体在对哲学的普遍无知之外,何以会再有一层对「自身对哲学普遍无知」一事的普遍无知。
这个悖论的源头,在于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问题根本上是规范性层面的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着力点则落在描述性层面的问题(descriptive questions)上。
描述性,有时也称「实然」,追问的是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个体的内心世界)之中究竟存在哪些事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哪些事件,以及作用于这些事物及事件的因果法则或统计规律;规范性,有时也称「应然」,追问的则是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应当如何行动,以及当我们在思考应当相信什么和如何行动时,究竟应当出示怎样的理据和完成怎样的论证。
对于上述区分,有两类常见的疑惑。一类疑惑是:诸如「上帝是否存在」这类问题,难道不是关于世界上究竟存在哪些事物的描述性问题吗?哲学明明一直在讨论诸如「上帝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又说哲学问题根本上是规范性问题呢?
另一类疑惑是:科学研究难道不是常常告诉我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比如应该少吃高盐食品否则对健康不好、打雷时不应该在大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劈中等、税法不应该采用累退制否则会拉大贫富差距)吗?甚至不是有人宣称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从来不可能「价值中立」吗?认为科学根本上着力于描述性问题而非规范性问题,是否太过陈词滥调?
先回答第一类疑惑。首先,与「以太存在」、「电子存在」等科学假说相比,「上帝存在」假说缺乏任何可以有效检验的因果推论。我们虽然无法用肉眼看见电子(以及曾经猜想的以太),但是可以通过衍射实验、光速差值实验等等,考察理论假说与现实的吻合度。「上帝」则不然,作为假想中一位超自然的行动主体(supernatural agent),任何看似与其存在相悖的经验现象,都可以千篇一律地用其(原则上可以不为人类所知的)意图与能力来解释掉:比如对于「古生物化石显示物种一直在演化,而非如《圣经》所言自创世以来一成不变」,有神论者只消答以「这一切都出自上帝的预先安排」即可。至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预先安排、《圣经》所言创世过程究竟是实载还是隐喻,这些技术细节完全可以由有神论辩护士们随意填充。
这样一来,就算无神论者驳斥了「上帝存在」的所有「经验证据」(比如某些信徒所声称的亲身体验到了神启,其实只是常见的心理幻觉机制在起作用),顶多也只是双方扯平而已。如果只在经验现象层面做文章,有神论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唯一的办法是去追问:当我(在经验证据永远不足的条件下)相信有神或无神时,究竟是出于哪些前哲学的直觉(pre-philosophical intuitions)?这些直觉涉及到哪些关键概念、暗中依赖于对这些概念的哪种定义或理解?我在其他某个议题上的直觉,是否同样涉及到这些概念,同时又暗中依赖于对这些概念的另一种定义或理解?当我同时持有的这两部分直觉相互发生冲突时,我应该舍弃或修正其中的哪一部分?这种舍弃或修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会如何影响到我在二者之外的其他议题上的直觉?——就这样,哲学通过概念的澄清,思想实验的挑战,论证的构建、反驳和修正,让所有相关的直觉和信念接受反思的洗礼,最终达到一种融贯而稳固的「反思平衡态」(reflective equilibrium)。
在前面提到的「宇宙论论证」中,我们已经看到哲学家如何从「宇宙不能不有一个肇因和开端」这个普遍的直觉开始,追问「肇因」究竟应当如何定义比较合理、是否应当承认存在不需进一步解释的「原生事实」、究竟怎样的解释构成一种好的解释等一系列认识论层面的问题。
类似地,我在《上帝与罪恶问题》一文中简要介绍过,「罪恶与苦难问题」对有神论的挑战,以及有神论者试图做出的回应,无不要求我们对认识论与道德层面上许多相互冲突的直觉进行修正和取舍,比如:怎样的苦难算是「平白无谓的」苦难;上帝的全知是否与人类的自由意志矛盾;被预先决定了的意志是否还能作为分配道德责任的根据;对有能力阻止的无谓苦难袖手旁观是否合乎道德;道德应当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如果把「全善」属性从「上帝」概念中剥离,我们还有理由(在永远缺乏经验证据的条件下)相信他的存在吗;哪些事实(facts)可以被当作理由(reasons)来使用;「充足理由律」站得住脚吗;怎样的理由算是好的理由;等等。
可以注意到,这一连串的追问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把本来看似关于「世界上究竟存不存在某某东西(比如上帝)」的问题,变成了关于「我们究竟应当被什么样的理由说服,去相信(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某某东西(比如上帝),并按照这种信念来行动」的问题。
换句话说,哲学并不是要试图「验证」某个命题与经验世界之间是否存在「描述性对应」(descriptive correspondence)。这种验证,是科学的工作:比如,倘若用合理设计的实验否定了以太假说的种种因果推论,我们便认为「以太存在」这个旨在描述经验世界的命题,并不真正对应于经验世界的现实,而它的反题「以太不存在」,则与经验世界存在描述性对应;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便积累了一项关于经验世界的新知识。哲学思辨并不具备验证此类经验性命题真伪的功能,也无意插手这种经验性的验证。
然而并非所有命题都旨在给出关于经验世界的描述,也并非所有旨在给出这种描述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手段加以验证。当某个命题与经验世界之间的描述性对应(暂时或永远)无法验证时,或者当某个命题根本不是一个描述性命题时,其合理性便落入了哲学的研究范畴,接受两个层面的追问。
其一,对于这个命题的信念,在认识论规范性层面(epistemic normativity)究竟具有怎样程度的合理性;亦即,在缺乏可验证性的条件下,我们究竟可以有哪些理由、以及有多强的理由,去相信这个命题而不是它的反题。
其二,基于这个信念的行动(或行动准则),在实践规范性层面(practical normativity)究竟具有怎样程度的合理性;亦即,我们究竟可以有哪些理由、以及有多强的理由,去采取这种而非那种行动。
所有哲学问题的「哲学性」,都体现在围绕这两类规范性的或明或暗的追问。
四
哲学并不只是「原型科学想法」的孵化器
理解了哲学内在的规范性,种种关于哲学的误解、关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误解,便可涣然冰释。比如常有人指责说:哲学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展,还是在反复读古人写的那些书、问古人问过的那些问题,不像科学那样不断超越前人、不断积累知识、不断推动技术创新。
这话只对了一半:科学确实在认识与改造经验世界上突飞猛进,而哲学也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但这是因为科学本来就旨在研究描述性层面的问题、旨在检验理论假说与经验世界之间的描述性对应,并藉助这种描述性对应介入经验世界的因果链条。
相反,哲学旨在研究规范性层面的问题,关心的是各种规范性立场的合理性,通过建构和拆解论证,来辩护或挑战这些立场;所以哲学积累的「知识」,并不是关于经验世界中的事实与规律,而是关于各种规范性立场背后的理由与论证、理由的强度、论证的漏洞。哲学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便体现在,我们为这些立场提出的理由与论证,从肤浅变得深入、从粗疏变得精密、从破绽重重变得无懈可击。不了解前人已经积累的哲学论证,以及围绕这些论证的辨析和辩驳,就会陷入像霍金回应「宇宙论论证」那样夜郎自大的局面。
再比如霍金所宣称的「哲学已死、科学代之」。这种观点的兴起不为无因,毕竟现代科学的诸多领域都从哲学中脱胎而出,历史上哲学家曾经争辩不休的各路「原型科学想法」(比如世界由哪些基本元素构成、生命是如何起源的、主导情感的区域究竟是心脏还是大脑、民主制是否必然导致僭政),最后都被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接手研究。按照这个趋势推论,岂不是哲学的领地要被科学不断蚕食以至于最终消失?
然而对「原型科学想法」的孕育与孵化,远非哲学工作的全部,相反只是派生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在采取行动时,需要以对经验世界的可靠描述为参考;然而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人类既有的经验知识与科研手段,远不足以支持对相关描述性命题真伪的检验,此时我们只能在日常观察与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尽可能合理地揣测相关命题的可靠性。这种「描述性对应暂时无法验证」的情况,便是哲学作为「原型科学想法的孵化器」这一功能的来源;由于这种不可检验性只是暂时的,所以一旦时机成熟、相关科研领域开始发展,哲学便会(也应当)把这部分工作让渡出去。
但除了这些暂时不可检验的描述性命题之外,还有诸多从根本上无法用经验手段检验的、看似描述性实则规范性的命题(比如「上帝是否存在」),以及诸多对这种描述性对应本身所依赖的认识论概念,做出更深一层的追问、理解与反思的规范性命题(比如「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实验这种手段的可靠性」)。哲学作为孵化器的功能,只有以这种更根本的规范性研究为基础,才得以可能;而这部分基础性的工作,也永远无法转手给科学来完成。
还有一种常见的看法:哲学家有必要懂科学,科学家没必要懂哲学。这话同样正误参半。哲学的发展,确实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积累;毕竟规范性讨论最终要回答的,是身处经验世界之中的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和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平衡,不能不将相关的描述性素材纳入其中;哲学家倘若不懂科学,只靠扶手椅上的思辨得出的规范性立场,很有可能确实「不接地气」。
与此同时,尽管描述性素材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在相关规范性问题上的直觉和判断,但它本身在规范性层面却是中性的、需要解释的,而这种解释又会回到规范性问题本身的争论上,因此实质上并没有推动问题的解决。霍金试图用当代理论物理的成果来回应「宇宙论论证」,就是一个例子。
再举一例:当代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经常有人声称,利贝特试验(Libet experiment)通过发现大脑信号活动总是先于个体有意识的动作意向,而「证明」了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也有一些量子力学家声称,他们提出的所谓「康威-寇辰定理」(Conway-Kochen theorem)「证明」了基本粒子和人类个体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然则这些所谓的「证明」,其实都已经预先接受了某种对「自由意志」的定义,而「自由意志究竟应该怎么定义」,本身恰恰是围绕自由意志的一大块争论所在,因此这些「证明」其实只是在循环论证而已。
反过来,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个体来说,哲学知识确实并不必要;毕竟对哲学缺乏了解的霍金、道金斯、泰森,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就科学的整体发展而言,哲学的支持却不可或缺。科学对描述性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必须以一定的规范性预设为前提:大到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自然主义承诺(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naturalist commitments),即相信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和活动完全遵循自然法则、可以且只能通过合乎自然法则的(而非超自然的)手段加以揭示;小到统计显著性达到多高才意味着结论可信,或者(特别在社会科学中)当无法进行孤立因素的重复实验时,如何阐释和辩护具体的因果机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哲学上的规范性反思。
爱因斯坦属于少数认识到了这一点的科学家。他在1944年写给年轻黑人哲学家罗伯特·索恩顿(Robert Thornton)的信中说:
「今天有太多人——包括职业的科学家——在我看来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深受其时代偏见的左右,只有历史与哲学背景方面的知识才能让人从这些偏见中独立出来。来自哲学视野的这种独立性,正是在我看来,一个只配称为手艺匠或专职工作者的人,与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在。」
“So many people today—and even professional scientists—seem to me like somebody who has seen thousands of trees but has never seen a forest. A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gives that kind of independence from prejudices of his generation from which most scientists are suffering. This independence created by philosophical insight is—in my opinion—the mark of distinction between a mere artisan or specialist and a real seeker after truth.”
爱因斯坦的这番话,或许显得太过清高傲慢(「照这么说,连霍金都只能算个手艺匠?」)。同时,相信不少人会反诘道:看看科学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多少实打实的好处,是哲学能比的吗?就算科学家们完全不懂哲学、没能摆脱时代的偏见、或者在讨论上帝有无的时候犯些初级错误,跟我们又有什么干系?
其实是跟我们大有干系的。这种干系,或多或少反映在我接下来要探讨的「霍金的社会悖论」上。